徐青:青山仰忠魂
给红军老战士黄火青立碑的那天,听说现场的人并不多。可这件事却传得很快,也传得很远。
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
用臧克家的诗《有的人》,来赞扬红军老战士黄火青,是再贴切不过的了。
黄火青是从湖北枣阳走出的高级领导干部,却最终长眠在故乡石鼓山一个石头缝里,开始甚至连一块墓碑都没有,他终生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色、用一生践行党的宗旨的风范,在他的家乡一直被人们口口传颂……
第一次去黄火青老家枣阳新市镇杨庄,是和几位朋友一起去的,去的那天上午正赶上当地的教育部门在开展一个活动,参加活动的师生队伍前头看不到头后头看不到尾,石鼓山山上山下红旗招展人头攒动,上山的路口很远都被堵的水泄不通。原打算上山祭拜黄老英灵的计划只好取消,我慢慢在村子里转了一圈后,找到了黄老身前的故居,见到了黄老的后人他的侄孙黄德林。
院里挤满了人,黄德林两口子回答着人们各种各样的提问。我里里外外看了个遍,黄火青的故居还完好保留有四间坡房,每间房屋进深不少于八米,房前屋后供人居住的院落大概350平米。院内向西,是一片桃树林。大门口的上方既没写“黄火青故居”,也没写“黄火青纪念馆”,写的是“橙刺园”。飘逸洒脱苍劲有力的三个大字,一看便知出自湖北著名书法家杨斌庆之手,故居保持了原样极其简单。但人们想要了解的黄火青青少年时期生活学习的经历等,在这里都可以看到听到,完全起到了“故居”或“纪念馆”的作用,同时又不影响后人居住。看我看的认真,一位自称是黄火青家邻居的人告诉我,上级原本也是要建黄火青故居或黄火青纪念馆的,是黄火青生前坚决不同意才没有建。这种说法,我从枣阳党史办都得到证实。
新中国成立后,黄火青第一次还乡也是唯一一次还乡,是1979年10月。这年金秋,黄火青要回家乡的喜讯在枣阳传开后。街头巷尾,田间地头,大家都在谈论他,话题都是以他为中心。就连黄火青,平日里吃什么,大家都很关心。村里有两位老汉,曾为他是不是天天都在吃粉条子炖肉,而争得面红耳赤。
黄火青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红军时期,他先后担任过团政委兼团参谋长、中央巡视员、军政委兼军政治部主任、军团政治部主任。长征路上,他坚持不骑马,一直把马让给伤病员。历经千辛万苦,一步一步坚定走完了万里长征。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随四方面军行动,因坚决反对张国焘另立中央和南下被撤职。抗日战争时期,任新疆反帝总会秘书长,延安军政学院副院长,中共中央党校秘书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热河省委书记、热河军区政委,冀察热辽军区副政委。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辽宁省委第一书记、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中顾委常委。
黄火青的老家,在鄂豫两省交界的桐柏山南麓,他家所在的新市镇杨庄就在石鼓山的山脚下。他们村的后边,是连绵起伏的桐柏山脉,从他们村往南直到枣阳城,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回到家乡的黄火青,对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分外亲切。他虽然回家乡很少,但一直关心着家乡,对家乡魂牵梦绕。那次回家乡时,老人家住在县委招待所,当晚激动得半夜睡不着觉。翌日天刚麻麻亮,他就穿戴整齐做好准备,老人家想尽快回到老家,尽快见到乡亲们。
回到家乡的黄火青,不顾年事已高坚持登上了石鼓山。石鼓山是他早年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他当年和他弟弟黄民钦在山上刻下的“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工农兵联合起来抗敌救亡”等宣传口号,现如今还清晰可见,被湖北省人民政府命名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黄家他的多位堂兄弟、也是当年跟他一起闹革命先后牺牲的烈士都长眠在这里,每一位烈土都立有墓碑。如今的石鼓山,松柏长青,果树满园。
伫立在石鼓山上,黄火青思绪万千满含热泪。他在缅怀他的这些兄弟、战友、革命同志的时候,总要想起牺牲在他乡的秦超等革命烈士。他深情地对身边的人说,他现在回来了,可秦超却永远也回不来了。枣阳县志记载,“秦超,原名秦志铭,枣阳姚岗镇秦岗村人…… ”秦超和黄火青同时入党,1927年又和他一起被党组织派往苏联学习军事。在班里,他任党支部书记,秦超任团支部书记。三年后回国,又同时被派往江苏南通红十四军,他任团政委兼团参谋长,秦超任团长。那时,敌强我弱,环境艰苦,他们经常吃不饱。在一次与强敌的意外遭遇战斗中,他和秦超战斗到最后,他不幸负伤,秦超壮烈牺牲。一个月后,在另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不省人事的他,被当地的老百姓就近掩护了起来。后来看情况紧急,老乡们又趁黑夜把他藏到芦苇丛中,他才捡回了一条命。
建国后,走上领导岗位的黄火青,一直坚持以红军老战士自称,不管在哪里工作,都把自已的一切交给党,都把人民视为自已的父母。在繁忙的工作中,他也时刻没有忘记牺牲的那些战友,将回忆他们的文章及时寄回他们的老家和他们牺牲地的党组织。1984年秋,听说秦超烈士的牺牲地南通市海门县重修了烈士的陵墓,他题写了“秦超烈士墓”5个大字。
黄火青的生活十分俭朴,那年秋天回家乡时,一直穿着一套蓝灰颜色的半旧中山装。枣阳籍领导时任襄阳地区行政公署常务副专员的胡久明曾回乡看望他,县委书记周本立忙完工作就去陪同他。周书记对黄老十分关心,每天早上见到他,都要问他睡眠的怎么样?黄老在告诉周书记睡得很好时,总还要提出要他每顿少上几个菜,比如晚上有一碗芝麻叶面条子喝就中了。周书记明白老人家的意思是让他注意节俭,在安排老人家吃上芝麻叶面条时,只安排几个小菜。像农村庄户人家待客时一样,既可口又不浪费,黄老十分满意。
这天晚饭前,周书记对黄老说,晚上去剧院看戏。听说晚上有戏看,老人家很高兴,但也很警觉,他怕是为他安排的少数几个人看的专场,因为他过去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立马提出要和大家一起看,还提出每个人都要买票。周书记告诉他,是县剧团正在上演的《朝阳沟》,而且戏票是花钱买的,一人一张。黄老这才高兴地说:“我们都是共产党的干部,像看戏这一类的小事,也不能马虎。老百姓看共产党,就是从我们这些人的一言一行中来观察的。
回到家乡,回到老庄子上,黄老热情地走村串户看望亲属和乡邻,与他们亲切交谈。他还专程到学校去看看,并同学校的学生席地而坐合影留念。他先幽默地对小朋友们说:“我是你们的老老师。”一句话,逗得陪同的周书记和师生们都忍俊不禁,老人家也开怀大笑。接下来,他深情的对同学们说,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长征路上,他和战友们经常吃草根吃树皮,很多人嘴里一边嚼着草根一边走路,有的走着走着就栽倒了,倒下了就再也没有站起来。
他和两位关心他生活的乡邻聊天说,粉条子炖肉也吃,萝卜白菜也吃,但他现在最喜欢吃的是芝麻叶。“有一碗芝麻叶面条子一喝,比坐上席吃桌子还得劲!”老人走南闯北几十年,坚持不改乡音,最后一句地道的家乡话,加上连说带比划,逗得满场大笑。
当晚,老人在侄儿黄佑勤家里,吃了一碗香喷喷的芝麻叶面条。据黄老的侄孙黄德林介绍说,那天晚上,听说黄老提出要吃老家的芝麻叶面条,没人安排没人通知,村子里家家户户做的都是芝麻叶面条。陪同他的领导和工作人员,跟黄老一样都吃的是芝麻叶面条。黄老走这家进那家,进进出出,一直都是笑呵呵的。
这次回乡,黄老看到家乡的巨大变化喜上心头,特意作词一首抒发心声:
去时麦如丝,归来果满枝。
战天斗地五十年,旧地一切不相识,醉米汁。
秃岭穿新装,河水奔山岗。
乌云妖雾齐消散,桃李万株竞芳香,还故乡。
几十年里,黄老一直关心着家乡的建设和发展。家乡办厂、修路、建学、种果树,都倾注了老人的心血。老人回北京时,乡亲们特意为他准备了一些土特产。可黄老什么都不要,走时,他只带了一包家乡枣阳的芝麻叶。
这天,是一个星期天,阳光灿烂,我邀约了枣阳党史办的原主任詹华如等朋友一起,第二次去黄火青的老家。为了避开人多,我们把时间安排在下午,车开到山脚下我直奔石鼓山山顶。石鼓山是一个相对平顶的山,东北高西南低,东西长南北窄,是桐柏山西南余脉最边上的一座山。
像坊间广为传说的一样,终身以红军老战士自称的黄火青,死后长眠在他老家石鼓山上的一个石头缝里。如果不是枣阳市民政局后来在这里为黄老立了一个半人高的墓碑,黄老的陵墓什么痕迹也没有。
当乡亲们听说,黄火青为了不占用耕地,决定百年后要把自己的骨灰埋入石鼓山上的石头缝里时,很多人不理解想不通。乡亲们议论说,坟头再多也不会多他呀?就是大家都没位置也不能没有他的位置呀!说什么也不能让他去钻石头缝。这些话传到黄老的耳朵里,他对乡亲们很理解很感谢,但他钻石头缝的决心丝毫没有改变。
黄老耐心地给大家解释,反复做说服工作。人吃五谷杂粮,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死去的人总是比活着的人多。如果人死后都要选个好位置,都要堆个大大的坟墓,要不了好长时间,我们的后人就没有土地可耕了,死去的人怎能跟活人争地呢?
杨庄村半数姓黄,黄家在村里是大户,族人中的几位老者,相邀一起找到黄火青说,你带头钻石头缝,那我们咋办?黄老认真地对他们说:“你们想跟我一起钻我欢迎,你们不想钻我不勉强。石鼓山脚下位置也不少,反正谁都不能去占耕地,谁要是占耕地躺到耕地里去了,我就把谁扯出来。”说完,他爽朗地大笑起来,笑声中传递着一个共产党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者的乐观和自信。
当很多人生前花巨资,为自己买墓地修坟墓时,一个老红军老革命副国级干部,却在考虑不能为埋坟再占用越来越少的耕地,还说服乡邻们支持自己。生活中带倾向性的很多问题,特别是那些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习俗,人们认识到它的危害很容易,但从自己做起由自己带头来纠正却很难。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红军老战士黄火青同志做到了。
黄老是1999年99岁那一年的初冬,在北京因病逝世的。他死后,骨灰从北京八宝山运回,埋在了他家房后石鼓山的一个石缝里。实现了老人家生前的遗愿,既入土为安叶落归根,又不占后人一分一毫的耕地。
山上游人不少,上山的男女老少,都要给黄火青瞌头或鞠躬。旁边不远处,一个小伙子在给眼前的一群人讲着什么,我也凑上去听。原来,小伙子在给大家讲石鼓山的来历。石鼓山原来不叫石鼓山,山半腰有一块又光又亮的地方,用石头敲击时轰然有声,且酷似鼓声,声音清晰传递很远。黄火青小时候有很多童年伙伴,他就用敲石发声的办法把伙伴们约出来玩。当年闹革命秘密建立党团组织时,黄火青和他的战友们,也是用敲石传声的办法,通知大家集合开会。遇到紧急敌情时,也是用这一办法,通知大家做好准备或转移。或许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石鼓山的名字在当地就叫开了。
黄火青的墓碑很矮,只有多数墓碑的一半高甚至一半还不到,就是这个不显眼的小墓碑,还是枣阳党史办和民政局,根据老百姓的意愿,经过长时间争取才立的。黄火青既希望百年后魂归故里入土为安,又希望不占用一分一毫的耕地丧事从简。说白了,他就是要在这方面带个头给大家做个榜样,他认为由他在家乡来带这个头最合适最有说服力。黄火青生前是个言行一致说到做到的人,可生前决定的事身后能不能兑现呢?所以,他做出这一决定后,在向上级党组织家乡党组织汇报的同时,也向他的亲属特别是子女们,还有老家的有关人员都一一作了交代,临终前又向儿子黄毅成女儿黄易宇等子女特意叮嘱了此事。
黄火青的骨灰从北京运回家乡的那天,乌云低垂,天阴的像个水碗,骨灰入土安葬时知道的人很少,他老家新市杨庄的乡亲们也是临时才知道的,现场既没有锣鼓家什,也没有喇叭响器,杨庄的乡亲们能走路的有一个算一个都上山了。乡亲们见证了一个老红军老革命、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最为简单的安葬过程,以至于安葬完毕后,很多人问:“这就完事了?就这么简单?”黄老入土的这天,天一擦黑就开始飘雨,雨丝一会长一会短,雨不大却纵情地飘洒了一夜。乡亲们说,是上天在整夜哭别黄火青。
黄老为人民打江山时九死一生,为人民坐江山时鞠躬尽瘁,建国后几十年仅退休后回乡一次,回到家乡黄庄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而今,最终还乡叶落归根了,不仅不占一分一毫的耕地,他选择的属于自己的仅仅是一个石头缝,既不影响长树也不影响长草。黄老的陵寝没有坟凸也没有墓碑,将来家族后人和杨庄的乡亲上山祭拜忠魂时,偌大一个石鼓山到哪里去寻找他呢?乡亲们把黄老的骨灰安葬好后,都久久不愿离去。“呜啊——”不知是谁,倏地一声忍不住的悲鸣,仿佛从天而降。瞬间,现场哭声一片……
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在当地传开。有的是出于对老红军的敬仰前来祭拜,有的或许是要到现场看看到底是真是假,更多的人则是带子女孙儿来寻觅一个伟大人物的人生轨迹,希望自己的后辈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积极向上拼搏进取。从那时开始一直到现在,红军老战士黄火青的老家杨庄和他的长眠地石鼓山,自发成了一个远近闻名的红色旅游景点。来这里瞻仰和旅游的人,大都还喜欢鄂北的农家饭,不少人点着要吃黄老生前喜欢吃的芝麻叶面条,自然也带动了杨庄一带的餐饮业。乡亲们说,黄老驾鹤仙逝已多时,他生前心里都装着人民,死了还在为家乡的人民祈福。
生前一直吃芝麻叶,死后坚持钻石头缝,黄火青朴素的做人情怀,在教育和感动了社会的同时,很多人对这一结果却接受不了:“为什么黄老连个墓碑也没有?”当大家知道了这正是黄老生前的特意安排时,很多人虽然感动的落泪,但人们对这一结果还是不能接受。一传十,十传百,这事很快在方圆上百里传开。多年来,老百姓强烈要求给黄火青立碑,有近处的,也有远处的,有多人相约一起为这事找到了镇政府,也有人找到有关部门提出要自己出钱给黄老立碑。镇政府在耐心向大家做好解释的同事,及时将这事汇报到市政府,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也正是两级政府一直期望的。很多领导也感觉到,黄老是在用自己的行动影响和带动大家,移风易俗丧事从简,保护越来越少的耕地。在黄老连个坟凸都没有的陵寝旁立个碑,不是可以更好地宣传黄老的风范吗?
枣阳民间立碑一般家庭选择的碑高是1.1米至1.9米不等,也有碑高2.1米,甚至更高的,民政局决定取其中给黄老立个1.5米高的碑。一边是老人的临终遗言,一边是民意难违。经市委市政府多方考虑和协商,后来黄老的家人经过商量,只同意立一个半人高的碑。墓碑的正面,只有五个字:“黄火青墓碑”。墓碑的背面虽然字不少,但人们看后能清晰记得的,也是五个字:“红军老战士”。
由于既没有举行官方仪式,也没有按民间立碑的规矩办。给黄老立碑的那天,像他骨灰入土的那天一样,现场除了民政局的两位干部,和黄老的几位亲属,其余都是黄老老家杨庄临时得到消息的乡亲们,立碑的过程及其简单。也许是巧合,也许是民意感动了上苍。上午立碑,下午天就小雨。
农历丁酉年寒露这天,我回老家枣阳时,开车在枣阳城四周转了转。我是在枣阳城长大的,在我的印象中,枣阳城四周地边和耕地中间有很多很多的坟凸,仿佛是一夜之间,这些坟凸都没有了。
站在石鼓山顶,我目视着西北边的赤眉山,仰望着东北边的桐柏山,我的思绪回到了乌云聚集、长风激荡的年代。镌刻在石壁上年代久远的标语,隐现在石头间的茅封小路,傲然挺立的株株翠竹,耳边传来的阵阵松涛……我听到的是惊雷,看到的是火炬。长征路上、抗日前线、平津战场、辽河岸边、特别法庭审判大厅,黄火青的一个个身影,像电影镜头一样在我眼前晃动……
人们把他摔垮;
给人们作牛马的,
人们永远记住他!”
树木葱茏。说着说着清明节就快要到了,清明节回乡时我打算再去给黄老扫墓。红军老战士黄火青仙逝已有10多年的时间了,在他的家乡湖北枣阳,他就像一颗永不陨落的星辰高悬在天空,闪耀着恒久的光芒。
作者简介:本名徐青松,曾用笔名春雨。武汉大学法学院毕业。早年当兵,历任连队战士、军校学员、部队干部。百万大撤军所在部队撤编转业回乡,先后在市委组织部、山区乡镇、文联等部门工作任职。迄今,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国防报、原武汉军区战斗报、农民日报、中国青年报、解放军文艺、北京日报、湖北日报、河南日报、报告文学、中华英才、八小时以外、散文选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作家网、中国军网、中国榕树网、大河网和家乡的襄阳日报等报刋网络发表散文、报告文学、人物故事、诗歌等各类文学作品千余篇。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风景这边》、《梦想成真聂海胜》等三部书,《梦想成真聂海胜》由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用繁体字版在香港再版,作为中华名人小故事中的一部隆重推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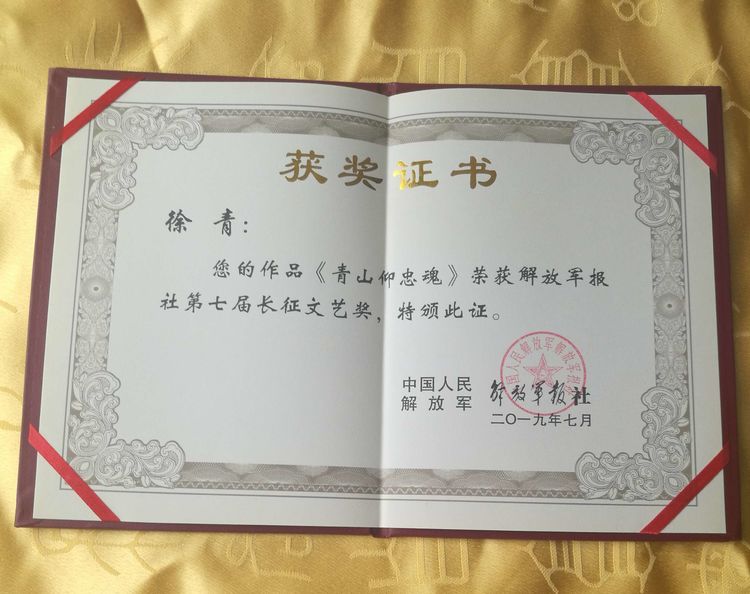



 鄂公网安备 42068302000124号
鄂公网安备 42068302000124号
